吴明强
父亲去逝后,母亲也离开了最后一个祖屋。祖屋成了一个没有人居住的空房子。
在故乡生活的日子里,我一共住过三个祖屋。
印象最深的是我童年生活的个祖屋。三间简陋的茅草房,住过这样房子的人都知道,这种房子不怕下雨就怕括风。一遇括大风,屋面上稻草就容易被掀起。尽管在盖屋参茅的时候,参茅师傅会把茅草一层接一层地扎紧扎牢,但终究难抵老天爷发大风。每年秋天盖屋的时候,母亲总是请最好的参茅师傅。在我很小的时候,来为我家参茅的多半是外公。外公是有名的参茅师傅。后来是一个我们叫他日新爷爷的老人,再后来叔叔也给我们参过参茅。由他们盖过的屋面平平整整,紧紧扎扎,看不到一根多余的稻草。但盖得再好的草房也经不住大风猛吹。经常是一括大风,母亲就领着我们兄弟姐妹搬砖头,找泥块去压住屋面上被风吹起来的茅草。有时风太大,会把茅草上的砖头掀下来,记得有一次从屋面上吹下的砖头还砸了人。
有了这样的经历,到我读高中、学习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时很有同感。“八月秋高风怒号,卷我屋上三重茅……”读了几遍我就能把这首诗背诵出来。这也许是我童年时代有这样刻骨铭心的经历吧。
小时候,看到少数人住瓦房,我常常想、我们何时也能住上瓦房呢?住在茅草房里心中总有一个住瓦屋的梦想。很多次,我把自己的十个手指头看了又看,希望十个手指头能有三个或者是四个“罗”来。因为我们家乡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:“一罗穷; 二罗富; 三罗四罗住瓦屋; 五罗六罗背长袋;”后面两句是什么我不记得了,只记得最后一句是:“十筲箕,骑马上阶基”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“骑马上阶基”是一件显赫的事,我也不去想那样,我只想能有瓦房住就足够了。
其实比我更想住瓦屋的,莫过于父亲和母亲,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的秋风茅屋破的日子。父亲和母亲更想住瓦屋,不光是为了他们自己,更多的是为了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。
可是在那样饥荒的年代,想做个瓦房谈何容易。一年下来,既没粮剩,有没钱余,不饿得太厉害就已经是够幸福的了。现在想起来,父母的决心真是大。虽然我没有听父母说过要做新瓦房,可我知道他们在作一些准备,收工之后,父母会把我们自家园子里的蔬菜种好,我们家的大白菜又大又白,既可以当菜吃,又可以拌饭吃。“小菜半边粮”说得就是用蔬菜顶饭吃。这样我们家一年下来多多少少可以节省一点粮食,可以请一些叔叔伯伯来帮我们家挑一些泥土作屋基。我的个祖屋紧挨着大堤,灶屋的屋檐比堤面高一点点,整个屋基有点矮。再做房子的话,父母都希望把屋基填高一点。我记得有好几年的秋天或冬天,我们家都会请人挑土。那些挑来的土先堆放在个祖屋的后门口,最后堆得有屋檐那么高,童年的我会经常爬到上面玩,去看绿了又黄、黄了又绿的田野;去眺望云卷云舒的天空;去听屋后竹林中的蝉鸣鸟叫。
记不清又过了几年,父亲从外面买了一些红瓦回来。那些新的红瓦颜色是棕红色的很漂亮。或许知道我家要做新房子盖红瓦时,心里特别高兴。搬红瓦时抢着去搬,每次搬一片,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打坏了其中的一片。红瓦买回来的第二年,父亲带领我们、又请了一些叔叔伯伯做砖坯烧红砖。那年父亲的一个朋友要从家乡搬到君山农场去,父亲又把他家的中屋柱排扇买了回来。中秋后我们家就开始动手筑新房,拆了个祖屋,把个祖屋后面的大土堆推平整,房屋地基比起原来的又高又大了许多。我们在这块地基上建了五间瓦房。从此我们家告别了风吹屋顶破的日子。我心中的喜悦恐怕不亚于海伦·凯勒次连惯地说出“天气很温暖”时的惊喜。
二十年后,由于弟弟筑楼房要地基,就把我们生活的第二个祖屋拆了,建起了一幢小楼房,弟弟的小楼房比起我们家第二个祖屋来气派多了。弟弟不免有点喜形于色。母亲总是平静的说:“是你们现在赶上了好时候哪……”我听了母亲的话,觉得母亲的话没有说完,但母亲总是淡淡地说完这一句就不再往下说了。或许是母亲没有让我们小时候住上小楼房有点遗憾吧。是啊!我们是赶上了好时代,要是父亲和母亲也赶上现在一样的好时代,凭父亲和母亲的坚毅、勤劳和不怕苦的精神、是完全可以象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建一栋有模有样的楼房的。
我家的第三个祖屋是后来父母为了独居建筑的三间青瓦房,房子虽然简陋,父母收拾得干干净净,祖屋的禾场前面是一个上百亩水面的大水塘,象一个湖一样,住在那里冬暖夏凉。在祖屋的后面父亲还挖了两个小小的鱼塘。我带女儿和爱人回家的时候,父亲立马提起他的鱼网在小鱼塘里撒一网,那些活蹦乱跳的小鱼经母亲简单的烹调后,变成了鲜嫩无比的美味佳肴。
大学毕业后,我在外面住过十多种不同的房子,应该说这些房子都比祖屋好,不知是什么原因,总找不到我住第二个祖屋的那种喜悦和温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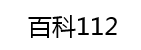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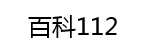 3分钟学会“决胜麻将别人开挂怎么看”(确实是有挂)-抖音官方" data-original="https://www.baike112.com/css/1.jpg" />
3分钟学会“决胜麻将别人开挂怎么看”(确实是有挂)-抖音官方" data-original="https://www.baike112.com/css/1.jpg" />